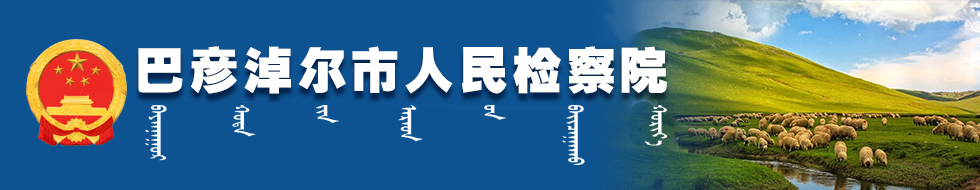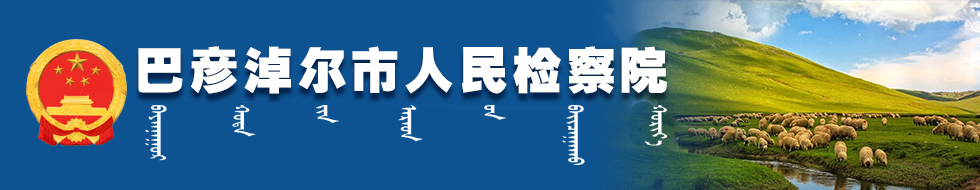阴山是一本被风、被雪、被马蹄、被凿刻、被吟唱反复修改的史诗。
它的每一道褶皱里,都住着一个曾经的民族;它的每一块岩面上,都叠印着不同语言的祷词。
——编者
圣山与家园:阴山之名与千年游牧记忆
孟长云(临河)
阴山山脉横亘于内蒙古高原南部,如同一道巨大的屏风,分隔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。这座山在不同民族口中有着不同的称呼——匈奴人称其为“祁连山”,意为“天山”;突厥人呼之为“于都斤山”,将其视作神圣之地;蒙古人则延续了“阴山”的称谓,在蒙古语中,阴山被称为“达兰喀喇”,既描绘了其重峦叠嶂、巍峨深沉的地貌特征,又为这座圣山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。
值得注意的是,阴山在历史上曾被称为“阳山”。这一看似矛盾的称谓实则为中原王朝视角下的地理标识转换。《史记·蒙恬列传》载:“秦已并天下,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,收河南。筑长城,因地形,用制险塞,起临洮,至辽东,延袤万余里。于是渡河,据阳山,逶迤而北。”此处“阳山”即指阴山北段。汉代沿袭此称,《汉书·匈奴传》亦有“北益广田至胘雷为塞,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”的记载,胘雷塞位于阴山北麓(即狼山—哈鲁乃山一带)。从地理方位看,中原王朝北上经略时,阴山位于河套之北,山南为阴、山北为阳,故称“阳山”。这一命名既反映了王朝疆域扩张中的地理认知调整,也揭示了阴山作为游牧与农耕文明互动前沿的复杂性——同一山脉因视角转换而被赋予截然相反的称谓,恰是其在历史上多重身份与意义的缩影。
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在其著作中曾精辟论述:阴山不仅仅是一条地理分界线,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接触带。在这里,两种文明不是绝对对立,而是形成了既冲突又互补的独特关系。这一见解深刻揭示了阴山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。
阴山之名,最早见于《汉书》:“匈奴失阴山之后,过之未尝不哭也。”汉字“阴”指山脉位于中原之北,背阳向阴,体现了中原农耕文明的地理视角。然而对北方游牧民族而言,这座被称作“达兰喀喇”的山脉拥有更为丰富的意涵——它既是神圣的祭祀场所,更是赖以生存的家园。
公元前2世纪,匈奴冒顿单于统一大漠南北,阴山成为匈奴帝国的重要根据地。匈奴人每年定期在阴山举行祭天仪式,《汉书·匈奴传》记载:“岁正月,诸长小会单于庭,祠。五月,大会龙城,祭其先、天地、鬼神。”祭祀之日,单于立于山巅,以白马为牺牲,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,将马血洒向空中。血珠在晨光里碎成雾状,游牧者称之为“天饮”。他们相信,那一刻祖先之灵会沿着山脊的铁锈色岩面飞驰而下,与族人同饮同舞。
从考古发现看,阴山地区不仅是游牧之地,也是早期金属冶炼的重要中心。位于阴山西段的霍格乞铜矿,早在公元前数世纪就已开始被开采。考古学家在古矿址发现了大量古代采矿坑道、冶炼遗址和青铜作坊,见证了北方游牧民族辉煌的青铜文明。匈奴人利用这里的铜矿资源,铸造出独具特色的青铜器,这些器物以动物纹饰为特征,造型生动有力,既有实用兵器如铜刀、箭镞,也有祭祀用的铜镜、牌饰。
自20世纪50年代起,考古学家在阴山地区陆续发现大量岩画,凿刻时间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元朝时期。其中一幅“鹿逐图”令人驻足良久:三只巨硕的北山羊被猎人围逼至崖壁,羊眼以同心圆刻出,目光如炬;猎人则作蹲踞状,双臂张开,似在舞蹈而非杀戮。这是一种“交感巫术”——猎人相信,只要把成功的狩猎提前画在岩石上,神灵就会让岩画内容在现实中降临。这些岩画生动记录了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和宗教信仰,印证了阴山作为圣山的历史地位。
公元前119年,汉武帝派卫青、霍去病率大军北击匈奴,夺取阴山地区。匈奴人被迫北迁,失去阴山不仅意味着失去了最好的牧场和战略屏障,更意味着失去了祭祀的圣山,这是匈奴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
北魏时期,鲜卑人取代匈奴成为阴山的新主人。鲜卑人原本居住在大兴安岭地区,南迁后逐渐接受农耕文化,但阴山仍然是他们的重要牧场和祭祀场所。北魏皇帝多次巡幸阴山,并在这一带设立军镇,既防御北方柔然人的入侵,也保护了自己的牧业基地。在阴山北麓,流传着拓跋部酋长诘汾的传说。在一次狩猎中,诘汾于阴山北麓偶遇“天女”——《魏书》记载,天女披白鹿皮,乘白鹿而来,与诘汾结合,生子力微,是为北魏始祖神元皇帝。这个故事巧妙地利用了阴山的“过渡性”:山北是草原,山南是农田;山是游猎者的圣地,也是农耕者眼中的“塞”。
突厥人崛起后,阴山成为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争夺的前沿阵地。突厥人称阴山为“于都斤山”,视其为国家的神圣中心。突厥碑文中记载:“于都斤山乃国家所由统一之地也”“驻于此地,我辈永保无忧”。可见在突厥人心中,阴山具有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神圣功能。唐龙朔三年,突厥可汗阿史那骨笃禄在阴山黑沙城(今包头西)起兵反唐。他麾下有一支由阴山州都督府降众组成的骑兵。《通典》记载,这些骑兵上阵前不呼唐军号令,而是面向阴山主峰——海拔2364米的呼和巴什格——高声呼唤“博格达”(突厥语神山)。他们相信,山神会借给他们风一般的速度。
到了辽代,阴山成为辽国的重要牧地。《辽史·营卫志》记载:“辽国尽有大漠,浸包长城之境,因宜为治。秋冬违寒,春夏避暑,随水草就畋渔,岁以为常。”辽朝皇帝四季巡幸,阴山是他们的重要巡幸地之一。辽朝在阴山地区设立州军,既发展牧业,也进行农业生产,实现了农牧结合。
成吉思汗崛起前,克烈部王罕曾在达兰喀喇山举行忽里勒台大会。会上,萨满阔阔出预言:铁木真若得阴山以南,将得天下之半。成吉思汗后来果然先取阴山,再入中原。元代,阴山成为两都巡幸路线的“北阙”。皇帝每年四月自大都北上,经野狐岭、兴和路,过阴山,至上都开平。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在游记中写道:大汗在此山狩猎,见白隼击空,命侍从放鹰,所获猎物堆积如山。
明洪武年间,于丰州滩(今呼和浩特)置东胜卫,沿阴山修筑边墙,并在山口设置“镇虏卫”“玉林卫”。然而,弘治年间,土默特部俺答汗仍突破边墙,在阴山南麓的丰州滩营建“大板升城”(即后来的呼和浩特旧城)。
从语言学角度看,阴山一词在历代游牧语中的转译也耐人寻味:匈奴语或作“阗连”,鲜卑语作“祁连”,突厥语作“博格达”,蒙古语则称“达兰喀喇”。它们共同的核心音素都带有“黑色”“广大”“神圣”的复合含义。于是,山名在口耳相传中,像风中摇曳的经幡,每一次颤动都叠加一层新的敬意。
今天,当我们用卫星地图俯瞰阴山,会看到一条清晰的分界线:山之南,河套平原稻麦两熟;山之北,乌拉草原牛羊如云。无人机升上呼和巴什格之巅,镜头里出现的是风力发电机的白色森林,它们与古老的敖包、烽燧、岩画同框,像极了时间的拼图。当你在草原上,走进一座牧民的蒙古包,仍能听到熟悉的问候:“你从哪里来?”“我从山那边来。”山那边,仍是家园;山本身,仍是圣山。
阴山是一本被风、被雪、被马蹄、被凿刻、被吟唱反复修改的史诗。它的每一道褶皱里,都住着一个曾经的民族;它的每一块岩面上,都叠印着不同语言的祷词。地名考、史料、岩画、传说、诗歌……所有这些,不过是我们试图在史诗边缘写下的注脚。真正动人的,永远是山脚下那些普通牧人日复一日的生活:他们清晨推开门,看见山还在,便知道世界仍在;他们夜晚抬头,看见银河落在山脊,便相信祖先仍在。
于是,阴山得以超越“界山”“战山”“资源山”的功利定义,成为“圣山与家园”的永恒隐喻。
北假之地:阴山北麓的文明微光
刘嘉耘(前旗)
八月的乌拉特草原美不胜收,头顶是澄澈透亮的蓝,天边是生机盎然的绿,脚下是翠绿到不忍落脚的草地。
此行,我来寻找一个在史籍中惊鸿一瞥的名字——“北假”。它不像长安、洛阳那样承载着煌煌国史,也不似江南古镇萦绕着才子佳人的旧梦。它只是一个被遗忘在阴山北麓的古老地名,像一颗坠入历史沙海的石子,渺小却可能承载着远超我们想象的重量。
一
“北假”之名,最早见于《史记》。秦始皇三十三年(公元前214年),名将蒙恬北逐匈奴后,“自榆中并河以东,属之阴山,以为四十四县,城河上为塞。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、阳山、北假中,筑亭障以逐戎人。”这寥寥数语,如云中雁影的“北假中”,便是我们所要探寻的“北假”之地。它并非虚幻的传说,而是深深楔入历史地理的一个真实存在。
那么,这“北假”究竟在何方?历代学者钩沉索隐,逐渐将目光聚焦于阴山山脉北麓、高阙塞以东的一片广阔区域,大致相当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、中旗、后旗的北部,以及包头市固阳县的西北部。这里,正是中原农耕文明向北方草原延伸的“触角”,也是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板块碰撞、挤压、交融的前沿地带。
“北假”顾名思义,有“暂借”“假予”之意。这名字背后,藏着一种微妙的政治智慧与独特的地理认知。在中原王朝的视角里,这片阴山以北的土地,或许并非如河套平原那般是天生的“腹里”,而是一片从游牧文明手中“借”来的前沿地带。它像是帝国伸出的一只试探的手,既要紧握成拳,以武力守护;又要张开五指,接纳与融合。
历史的聚光灯,曾几次照亮这片“北假”之地。它最初的辉煌,与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紧密相连——秦始皇。他命蒙恬北击匈奴,夺取的不仅是“高阙”这样的军事要塞,更有“北假”这片广阔的缓冲之地。始皇帝的意图是清晰的,他要的不仅是一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物理防线,更是一个可以实际控制、进行农业屯垦,从而将帝国力量持续向北渗透的战略基地。
然而,秦祚短促,二世而亡。随着秦帝国的崩塌,“北假”重陷纷争。直至汉武帝时期,卫青、霍去病等名将数次挥师北进,才重新夺回这片土地,并置朔方郡,下辖十余县,其中许多县城,便坐落于“北假”之中。汉朝的经营更为系统化,大规模的军屯与民屯在这里展开。可以想见,当年的“北假”是怎样一派繁忙景象:田畴阡陌纵横,渠水潺潺流淌,谷粟在风中摇曳;城堡巍然,市井间夹杂着关东口音与河套乡谈,戍卒们日夜警惕着北方的动静;那些归附的匈奴部众,也在附近草场放着牛羊,参与着频繁的贸易。
二
秦始皇为何要耗费国力,命蒙恬“度河据阳山北假中”?这绝非帝王一时的心血来潮,而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冷静抉择。
“取高阙、阳山、北假中”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核心,在于构建一条立体的、纵深的防御体系。高阙塞是出击的拳头,是锁钥;阳山(即阴山)是天然的屏障,是脊梁;而“北假”,则是这强大臂膀得以伸展的坚实肩胛,是支撑前沿军事存在的战略后方与粮草基地。
阴山山脉,自古便是天然的军事屏障。但仅仅依靠山脉防守是被动的,匈奴骑兵来去如风,他们可以轻易绕过某个山口南下河套,威胁帝国的心脏。因此,最有效的防御,是前出。将防线推进到阴山以北,将前沿基地设立在“北假”之地,就如同在对手的门前设置了一座永不关闭的哨所。驻军于此,可以随时侦察敌情,威慑对方;屯垦于此,可以为前线部队提供粮草,减少从中原千里转运的消耗。
“北假”的设立,是中原王朝一次极具魄力的战略进取。它标志着农耕文明不再满足于划河而守,开始尝试以一种更积极、更具弹性的方式,来经营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。这里,是进攻的跳板,也是防御的纵深。其直接原因,是为了解决一个庞大的军事后勤难题。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驻守北疆,“暴师于外十余年”,粮草消耗是一个天文数字。若全靠从中原长途转运,路途遥远,耗费巨大,且易受攻击。于是,“因河为塞,筑四十四县城,徙谪戍以充之”的策略便应运而生。“北假”正是这一系列新城中至关重要的一环。在这里实行大规模屯田,可以实现粮食的就地生产、就地供应,为前线将士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大后方。
《汉书·匈奴传》记载,汉朝曾一次就调拨边塞谷米数十万石,以救济归附的匈奴部众,如此庞大的粮食储备,很大程度上便依赖于“北假”等地的屯田成果。而其深层意义,则远超军事后勤本身。它标志着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理,从单纯的军事防御,转向了“农战结合”的永久性经营。一道长城,可以暂时阻挡骑兵的冲击,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北方的威胁。而“北假”这样的屯田区,则是在进行一场更为深刻的“文明置换”。其设置原因,深刻而明晰:其一,地理的必然。阴山山脉如同一道巨大的屏风,分隔了湿润与干旱,农耕与游牧。然而,山脉并非铁板一块,其间沟谷纵横,形成了南北交通的天然通道。控制了阴山北麓的“北假”之地,就等于扼守住了匈奴南下河套、窥伺中原的主要通道,将防御前沿主动推进至漠南,为河套平原及关中地区赢得了宝贵的战略缓冲。其二,经济的必需。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。数十万大军驻守边塞,后勤补给是生命线。若全靠关中转运,路途遥远,损耗惊人。“北假”之地,虽不及河套水草丰美,但得山麓泉水与季节性河流滋养,具备发展灌溉农业的潜力。于是,“徙谪实边”“屯田北假”成为必然之选。帝国的官吏、戍卒以及被迁徙的民众,在此开凿水渠,引水溉田,将中原的农耕技术根植于这片土地上。其三,文明的深入。这或许是“北假”更深一层的历史意义。秦帝国在此地的经营,是一次华夏文明向北方游牧文化区的主动延伸与深度楔入。它不仅仅是筑城戍守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移植与文明的对话。中原的农耕聚落、行政管理模式、生产技术乃至文化习俗,随着屯田的展开,在这片原本以游牧为主的土地上生根发芽。这是一种无声的宣告,也是一种艰难的融合。
三
“北假”的设置,其重要意义不在于它见证了多少次战争,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在战争间歇,文明得以彼此打量、试探乃至学习的可能。它不是一堵绝对的墙,而是一扇半掩的门。
“北假”的试验,虽然随着秦朝的骤亡与汉初的收缩而一度中断,但它播下的种子,却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两千年中国的历史走向。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,再次经略北疆,卫青、霍去病北击匈奴的赫赫武功,其行军路线与后勤基地,或多或少都依托于对“北假”这类地区的控制经验。汉朝在此设立的五原郡、朔方郡,其管辖范围便深深嵌入这片土地,将“北假”真正纳入了帝国的郡县体系。
更重要的是,“北假”奠定了一种中原王朝经营北疆的范式:即单纯的军事防御与积极的屯垦实边相结合。这种范式被后世王朝反复借鉴、完善。从汉代的屯田卒,到唐代的屯防军府,再到明代的卫所制度,其核心逻辑一脉相承:让士兵在和平时期成为生产者,实现军粮自给,并以此为中心,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移民社会,从而实现对边疆地区的长期、稳定控制。它告诉我们,一道真正稳固的边疆,不仅仅是刀剑划出的线,更是犁铧耕出的田,是炊烟升起的家。
它的地位,因而超越了地理范畴,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。它是中华文明强大的吸附能力与拓展弹性的早期证明。在“北假”之后,无论朝代如何更迭,中华文明的版图在北方总保有一种强大的向心力,总能将这片曾经的“边缘”一次次地拉回“中心”的辐射范围,最终凝结成不可分割的肌体。
这种“前进防御”与“文化浸润”相结合的理念,贯穿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边疆史。
四
这是一个地理的过渡,更是文明的交界。
“北假”作为秦汉时期的特定行政区划,其名虽在后世渐渐湮没,但它所代表的边疆治理模式与文明交融态势,却如同一条伏脉千里的暗河,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历史走向。
首先,它奠定了中原王朝经营北疆的一种基本范式。即“前进防御,屯垦实边”。从赵武灵王的“胡服骑射”开辟阴山疆土,到秦汉的北假屯戍,再到后世的军镇、卫所制度,其核心思想一脉相承:将防御前沿推至自然地理的极限,并通过军事化屯垦,实现长期驻守与经济自给,化边疆为内地。这一模式,极大地增强了中原王朝的战略纵深与韧性,为农耕文明的存续与发展提供了保障。
其次,也是更为重要的,“北假”之地成为了一条持久而旺盛的文明融合通道。它像一座巨大的、无形的“渡桥”,南北两侧的文明要素,通过这座桥梁,源源不断地进行着双向的流动。南方的农耕技术、金属工具、礼仪制度,通过戍卒、移民和贸易,传入北方草原,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。而北方的畜牧经验、特产乃至艺术风格与勇武精神,也深深地渗透进中原文化肌体之中,为之注入了新鲜而强悍的血液。
最为典型的例子,莫过于后来兴起于这一地区的鲜卑拓跋部。他们正是首先活跃于阴山北麓及代北之地,充分吸收了多种文化养分,才得以建立起强大的北魏王朝,并最终实施影响深远的孝文帝汉化改革,为隋唐大一统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可以说,没有“北假”这类边缘地带长久以来的融合与酝酿,就不会有后来中心地带更加恢宏的文明盛景。
“北假”的屯田经验,被汉代全盘接收并发扬光大。汉武帝时,曾“发谪戍屯五原”,后又“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”。规模更大的屯田活动在此展开,使得阴山北麓的防线更加巩固。汉代的“北假”,依然是支撑对匈奴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。直至东汉,乃至魏晋南北朝,虽然中原扰攘,但每当北方政权有能力经营边塞时,“北假”所在的区域,始终是关注的焦点。从汉代的屯田河西四郡,到唐代的节度使兼领营田,再到明代的军卫屯田,乃至清代的移民实边,其核心逻辑都与“北假”一脉相承:军事存在与农业生产相结合,国家动员与民间迁徙相补充,以此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控制与长期开发。“北假”是源,后世是流。
更重要的是,这片土地所促成的民族融合,如同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,激起的涟漪千年未息。那些在“北假”及类似地区形成的混血族群,那些在交融中产生的新文化特质,最终都如同涓涓细流,汇入了中华文明的浩荡主脉。北魏的鲜卑汉化,蒙古帝国对中原制度的采纳,清朝的“满汉一家”,其底层逻辑,早在“北假”这样的边境地带,进行了无数次小规模的预演。
五
行走在阴山北麓,抚摸着那些被风沙侵蚀的古城墙基,我心中涌起的,并非仅仅是怀古的幽情,更是一种对文明本质的深思。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,其实是一片文明的沃土。它孕育的,不是哪一个王朝的霸业,而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伟大历史进程。那吹拂了千年的北风,带来的不只是沙尘,更是文明交融的古老信息。它提醒我们,今日我们所享有的这个博大而包容的文明共同体,其根基正是由无数个像“北假”这样的地方,以及生活在那里的无数无名先民,用他们的生活、汗水与血脉,一点一滴,共同奠定的。
文明的生命力,恰在于此。在“北假”这样的文化交错区,农耕文明的坚韧与秩序,游牧文明的机动与包容,在这里相互淬炼,最终共同锻造了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不断新生的强大基因。
“北假”早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,但它所见证和参与的那个伟大进程——中华文明在碰撞与融合中不断拓展、丰富、重塑自身的进程,却从未停止。这或许就是阴山北麓留给我们的,最珍贵的文明微光。即它所代表的那种开拓、包容与融合的智慧,如同阴山一般,巍然屹立,成为我们民族记忆中,一道永不熄灭的文明之光。这缕微光,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里,成为一种内在的、面对异质文化时,既能坚守本色,又敢于吸纳创新的精神基因。而这,或许是“北假”之地,留给我们最宝贵、也最永恒的启示。